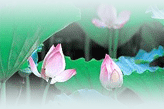|
||||||||||||
|
2010年1月,“《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套历经四代科学家、耗费半个世纪完成,拥有126卷册、5000多万字、9000多幅图的浩繁巨制,终于实至名归。然而,当无限荣光来临时,一些历经千辛万苦、甘于寂寞的科学家已远离尘世。担任该志第一届主编的陈焕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一同被授予这项荣誉的华南植物园胡启明研究员、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研的吴德邻研究员和华南植物研究所前所长梁承邺研究员、曾在陈焕镛身边工作的黄观程研究员,日前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他们的专业解读勾勒出一个更加立体生动的陈焕镛。 1 引领植物学走上现代之路 南方日报:1919年陈焕镛回国时,中国现代植物学研究“一穷二白”,但他在晚年作为首任主编参与了世界最大的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如何评价陈焕镛在学科建设中的价值? 梁承邺:他的学术地位,我认为冠以中国现代植物学主要奠基者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在他这批人之前,中国植物学尚未进入现代范畴。80多年来,植物学的分支越来越多,但中国植物学的源头是从他们的分类研究、资源搜集开始的。 如何判断一门学科的形成有几个标准,应包括专业机构、专业队伍、专业刊物,在这些条件下能持续产生有现代意义的一批论著和讲义。回顾一下就可以发现,在陈焕镛那个时代这些标准都符合。 首先看专业机构:中国两个最重要的研究所,1928年的北京静生生物所和中大的农林植物研究所。其次看专业队伍:民国时期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资源研究所中设有植物研究所,后来该院设评议会,代表三四十人中,有两个研究植物学,可见已经奠定了学科地位,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第一代植物学家的研究生也成为植物学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除此,陈焕镛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业植物分类学刊物。这样学科就基本形成了,而从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陈焕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日报:中国人关注植物有上千年的历史,诞生过《本草纲目》这样的重要著作,陈焕镛和同辈科学家如何超越传统的研究方法? 吴德邻:现代植物学按系统分类,古代按木本、草本等进行分类,古代的研究方法不能反映自然界的进化过程,西方的系统法则尽量反映这种进程,并且可以用化石、地质年代等证据来证明。 其次,现代植物学按照门、纲、目、科、属、种划分,有规范的国际命名法规,一种植物只有一个合法的名字。不像中国,不同地方对同一种植物的叫法就有可能不同。陈焕镛他们编撰的早期著作,已经完全按照国际规范的分类法,与《本草纲目》不可同日而语,他引领植物研究走上一条现代之路。 2 80年前即提出退耕还林 南方日报:陈焕镛的研究为今天的广东学术界留下什么遗产? 吴德邻:作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不但为广东,也为中国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现在的研究都在他们的基础上深耕。他的四大贡献显示出惊人的创新思想和超前意识,即使现在看来还是如此。 第一大贡献是,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就和秉志等6位科学家联合提出“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提案”,后获得通过。在此背景下,他继续提出在肇庆鼎湖山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设想,最后在国营鼎湖山林场划出17000亩建自然保护区,区内保存有典型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当地野生植物2400余种,有北回归线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之称。 而早在1930年,陈焕镛就提出资源的保护策略,提出要有公共供热、供水系统,提出森林资源保护要减少浪费,要注意副产品的开发,科学监管,实行可持续发展,限制工厂的烟尘,现在已经是共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需要反思。退耕还林我们做了没多少年,但这却是80年前陈焕镛提出的理念。可见其科学的预见性多么惊人。 第二大贡献是设立华南最大的植物标本馆。标本是研究植物分类的基础。在其不遗余力数度组队采集后,至1938年标本已达15万号,其中有和英、美等60多个国家交换的珍贵标本以及浸液标本。吴征镒院士认为,至1954年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分类学基础在当时已属全国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陈焕镛院士在标本馆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的结果。如今,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馆馆藏已达百万号,为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北京、昆明、广州)之一。 胡启明:他创建华南植物所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植物学,书籍、名词多是照搬日本的,教学用的标本要从日本进口。如果没有华南的陈焕镛和北京的胡先骕等老一辈科学家奠定了标本、图书、文献基础,并大力培养人才,《中国植物志》是不可能现在就完成的,更不可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华南植物园的标本采用严格的科学管理,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标本若被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标签贴在标本上;标本封套内还附上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不但使定名更准确,也为研究提供了条件。 高标准的管理为后来采用计算机管理标本打下了基础。几十年来,英、美、德、日等国专家参观后无不感叹其管理之完善。 吴德邻:华南植物园是他的第三大宝贵遗产,这是中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焕镛教授任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所长期间,就注意采集苗木、种子,开辟苗圃,设立植物园做研究之用,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1956年他亲自规划建设占地4500亩的华南植物园。目前植物园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徜徉其中。 他的第四大贡献是,创立了华南最有价值的专业图书馆。文献和标本是植物分类研究的依据,二者缺一不可。早在建所伊始他就设立了图书馆。据1937年统计,馆藏中、西文图书已达4000余部,中、西文定期杂志50种以上。许多珍贵的西方植物学文献均有收藏,如分别于1954年和1753年出版的林奈《植物属志》(Linnaeus·C,Genera Plantarum)和《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以及欧美植物分类学的重要期刊和中国古农书、方志、本草等重要文献。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经典著作对于后人进行植物学研究、编写植物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 痛心中国植物被外国采了200年 南方日报:与陈焕镛同一个时期,中国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植物学家,如钱崇澍、胡先骕、汤佩松、吴印禅、吴征镒、蔡希陶等,在这个相对冷清的专业里,为什么人才成批涌现? 吴德邻:早期研究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都是外国人。据不完全统计,自17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有16个国家约200人来中国调查植物资源,在200多年中,采了近100万号标本,上千种植物苗木和种子,记载新发现、新记录植物上万种,新属158个。 这些人中,大家熟悉的人有英国人汉斯(H.F.Hance)和汉姆斯莱(W.B.Hemsley),美国人F.N.Meyer、法国人J.P.A.David和J.M.Delavay、俄国人C.J.Maximowicz、奥地利人H.Handel-Mazzetti、日本人早田文藏和山本由松。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植物学家都很熟悉中国的园林花卉和经济植物,他们到中国采集、研究植物的背后都隐藏着战略或经济利益。 胡启明:当时欧洲流行一个说法,“没有中国的花卉,不成为庭院”。植物学,并不如普通公众认为的是个冷门,在国外一直是热门。当西方进入一个新的殖民地,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资源,包括矿产、文化、动植物等,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海关官员等,都为中国的植物资源惊叹,一批批远道而来,又一批批运走。 西方的每一个公园、植物园里,都有中国的花木,杜鹃、菊花、茶花等被大量引种。像猕猴桃就是从中国引种出去的,改良为商品在国外已有几十年,而我们才几年。陈焕镛他们回国时,中国的植物资源已经被国外采集200年了,你说他们不痛心、不感到迫在眉睫吗? 吴德邻:陈焕镛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时,就已立下了保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改变我国植物学研究落后面貌的志愿。他目睹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植物学家大量搜集我国珍贵植物出口,使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在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这些现实使陈焕镛深感痛心。 4 教学未废一日,育才毫无保留 南方日报:陈老一生科研、教学,未曾一日废离,很多学生在回忆文章中都讲到,他培养人才毫无保留。 胡启明:陈封怀、蒋英等第二代植物学家,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我听导师陈封怀先生讲过,他们师生时常打成一片,一有空陈老就会找他谈话,并经常请客。陈封怀先生自己成为植物学专家后,对导师始终非常尊敬。 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时,陈焕镛以自编的Chinese Economic Tree作辅导教材,这是英文版本的,在广西大学任教时,又自编《广西植物分科检索表》作为材料,遇到外语根基不好的学生,他都由基础教起,因人施教。 吴德邻:1955年,刚认识陈老时我是小字辈,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他任所长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他已是学术大家,但一有机会都不忘提携后学。 1962年我在编写《海南植物志》姜科的时候,在我所标本馆发现了2张从来没有见过的标本,1张采自广东信宜,1张采自海南保亭。后经过仔细研究后,确定它们为中国的新分布科——兰花蕉科,并且是两个新种,分别是兰花蕉和海南兰花蕉,其中兰花蕉现已被定为国家三级保护濒危物种。 当我向他汇报这一发现并把标本拿给他看时,他说北京植物所的汪发缵教授正好在这里,最好拿给他看看,后确认我的鉴定无误。我很兴奋,准备立即发表。陈老却不以为然:“兰花蕉科全世界只有1属数种,你既然已确定广东标本为新种,说明你对全世界的种类已有所了解,不如写一篇专著性论文,顺便讨论一下科的位置。” 我担心没有外国标本,陈老说,没有标本可以想办法。于是,他当即写信(由我执笔)给当时在印尼的华侨孙洪范先生,请他代为采集该科的标本。后来孙先生果然寄来了兰花蕉属的外国标本,这为我撰写论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30周年大会在京召开,经他安排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兰花蕉科植物之研究”的报告。由于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有重要意义,受到了同行的关注,这对当时身处逆境的我是一种鼓舞。后来他还亲自帮我修改英文摘要并安排于1964年的《植物分类学报》上发表。他热情帮助、循循善诱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黄观程:1955年夏我在北京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通知我立即到华南植物研究所报到,陈焕镛所长不久就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因为我是俄文专业毕业,他专门叮嘱我要好好学植物学、学英文、学拉丁文,并让我教其他科研人员俄文。 拉丁文是搞植物分类的必修语言,他在美国受的教育,英文、拉丁文造诣很高,相反,国内的学生大多欠缺这方面的训练,他就自己制作了卡片,一个字一个卡,法国、瑞典、英国等各国大家的用法他都抄下来,做了一抽屉。很多专家都是用他编的教材来接受拉丁文启蒙教育的。 5 讲道理的性情中人 南方日报:他的学术生涯以严苛著称,性情是否也如此? 吴德邻:陈老工作时可以日以继夜,但也有幽默轻松的一面,有时会喝杯小酒,讲讲笑话。我记得他讲过一个笑话印象很深,说他在林中解手,把帽子放在一根竹笋上,解完手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发现原来竹笋长成竹子了,帽子被顶上天了。 黄观程:我和陈院士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并不多,但到前苏联考察的3个月我们天天待在一起,所以印象很深。 有一次,他叫我去找一本植物学文献,我找了很久,等找到时,他有些生气,说我浪费了半个小时,原来是他写给我查阅的字条有个别字写错,如果是标本也许还可找到,但图书就难找了,因为书名错了就可能出现在很远的书架上,所以耽搁了不少时间,他知道情况后马上就向我道歉了。 在前苏联考察时,有天我们一起等车,他手上有英俄对照的小册子,一边看一边跟旁边的人聊起来,当时是5月份,天有点凉,我看他手上空空,就跑回去把他的大衣拿回来。一见面,他就批评我:“有没搞错,是我等你还是你等我?”等我把大衣给他,他又道歉了:“对不起,有时候是应该我来等你。” 批评归批评,道歉归道歉,他是个很讲理的人。3个月中,我学了不少。我们什么都聊,有一次,他说他对俄罗斯文学很感兴趣,但看的是英文版。我们高兴时还一起喝点酒。一次,他让我去买火腿等食品,可能当天有点心情不如意,提到华南植物所虽大,但不如北京,说我们也要做得更像样。等我买东西回来,他已经喝醉了。 还有件有趣的事,出国时我没有经验,只带了一条领带,他却带了好几条,看我来来去去都是同一条红色领带,就找出一条有植物图案的送给我,“你不能每天都戴一条领带,我送你一条。”那条领带很有朝气,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任公豆歌 ■胡先骕 粤中名山多奇峰,烟峦幻出千芙蓉。 韶雄远与庾关通,鸟道悬绝稀人纵。 千年古木如虬龙,时生佳卉罗珍丛。 风柯纷披叶葱茏,花翔如蝶酡颜红。 枝头来三白头翁,宛如幺凤栖刺桐。 是乃葛仙鲍姑所未见,名山久閟今初逢。 移根瑶圃光熊熊,一洗万国凡卉空。 自来珍物不世出,宜著篇什歌丰功。 任公德业人所崇,以名奇葩传无穷。 彩绘者谁澄如冯,赐名者谁陈韶钟。 注:1946年陈焕镛发现一种很特殊的豆科植物,创立了任公豆属,以纪念著名学者任鸿隽先生。此诗为胡先骕赞颂此事而作。 本版采写: 南方日报记者 林旭娜
|
|||||||||||||||||||||||||||||||||||||||||||||||